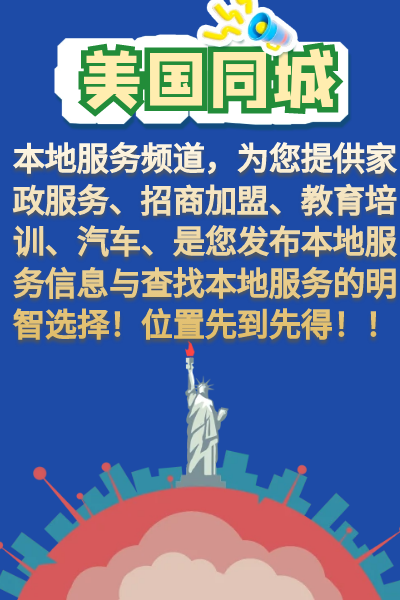
而下班时间是指在井下4点,从掌子面到地面最少得40分钟,再洗澡换衣服,再到队里碰个面(班后会)就5点多了。我开始还守纪律,等开完班后会才去吃饭。后来“油滑”了,一洗完澡,就跑去食堂买5个馒头一盘菜往饭盒里一装,边开会边吃饭。
从早5点半到晚5点半,一天两顿饭,间隔12小时,中间最多接井下冰凉的凉水喝几口,这胃受得了吗?有人会问:中间不带饭吗?没法儿带,因为是超级瓦斯矿,所以掌子面长年温度是10—18度,干活时穿小布衫,把棉袄随手放跟前。待避时(等放炮时)就把棉袄一穿,根本没有揣饭盒的地方,再说除非你把馒头绑腰上。否则一放炮全变样了,到处漆黑,你也根本找不到东西,所以时间长了,就饿习惯了。矿工是60斤定量,我基本早晚各一顿5个馒头(一斤),月月吃光。至于“开水”是一天送一次的,但是离工作面老远了,既舍不得那时间跑路,而且也是冰凉的。工作面除了“放炮”就是“攉煤”,那粉尘和烟雾比“沙尘暴”还多,所以“煤黑子”就是这么造成的。
杨姓女,住大明镇,丈夫原也在井下采煤,因为工伤所以调到供应处当装卸工,因为是跟车作业,所以三天两头儿出差。周围的老邻居还是大多在井下工作的。前面说过,采煤工下班到家都6点以后了,累得要死困得要命,吃点饭,再喝点小酒,和老婆孩子说不上几句话,就睡觉了。几千年的习惯,男的养家糊口,女的烧火做饭;夫妻关系就是男的舒服,女的伺候。至于“高潮”之类话,都是小知情调,更别提什么女人的“高潮”,那可是“羞”死人的“耻辱”。
和上班的比,家属的时间就空闲得多了。送走老爷们儿,还可以搂着孩子睡个回笼觉。因为大多是农村来的,文化不高,没有职业,既没有地可种,也没有什么副业可搞,所以七大姑八大姨的串门聊天,说书讲古和上街买菜就是一天的正事。(那时,还没兴打麻将。)时间长了,编个新花样,玩个纸牌,也没有大输赢。就是大家凑钱弄一桌饭菜,乐和乐和。
这杨姓女因为丈夫常不在家,所以更显得清闲,她家就成了邻近女子“俱乐部”。和她最要好的是隔街的李姓家属。老李家的,50来岁,因为头一个就难产,所以再没生过,一直很瘦弱。丈夫是矿山救护队的,也不常回家,宝贝儿子在外面工作。这俩女人在外人面前称“姑嫂”,没人时互相戏称“当家的”和“屋里的”。李姓家属很挂记这个女“当家的”,所以常把自己的钱和物拿来共享。积少成多,时间一长,就埋下了隐患。
这天,周末。李姓丈夫和儿子不约而同的回来了,儿子还带来了“对象”。老头挺满意这个“准”儿媳妇。就“命令”老伴“明天走时给带100元钱,再把早前买的一对耳环,作为聘礼给那姑娘。”他哪知道他家的钱和东西早“搬家”了。李女一听,顿时傻眼,真是快愁死了,急疯了。
晚上睡觉,李女特意安排丈夫和儿子睡东屋,她和准儿媳妇睡西屋。(那时,未婚同居等于流氓行为。)刚一落枕头,李女就悄悄地溜到老杨家想取回旧物,或研究对策。
杨女一听也急了,“耳环被妹妹拿回老家戴了,钱,也就够20-30,怎么办?”俩人,一会儿互相埋怨,一会儿又咳声叹气的拿不出办法,最后的“笨招”就是“死路一条”。杨姓女在老家作过豆腐,所以留有“卤水”。既然死意已决,老李家的抢先连喝几口,杨姓女也只得喝下剩下的。
这时,老李头和儿子已经开始到处找人了。因为老伴的神情,早就引起了老头的怀疑,碍于“准儿媳妇”的面,一直没机会问。老伴出走时,他以为是解手去,也没好意思跟,老半天没回来,可就着急了。只得捅醒儿子到处小声喊“老伴”和“妈”。
杨女听见了喊声,忙催老李家的回去。老太太这时已经开始糊涂了,勉强走出杨家的门,一拐弯,就摔倒在过道里了。正好丈夫和儿子找来了赶忙背回家,但是她身体已经开始僵直了。
眼看亲人不明不白地过世,老头和儿子都气疯了。二次找到杨家,拖起杨女就连踢带打,把女的打得呕吐了半天,反而拣回来杨女的一条命。
又好事又无知又下流的“群众专政指挥部”本来就不是正经人呆的地方,闻听此事,一本正经的喜出望外把杨女抓了去,专门问那些污七八糟的“细节”,杨女也自知这回难逃“法网”,为免遭皮肉之苦,只得跟着胡说八道,承认自己是“二乙子”,在“性欲难忍”之下“强奸了老太太”。这等新闻,太刺激了。于是在“送交”公安局之前,天天游来游去,仿佛革命高潮的到来。
后来呢?杨女由“群专”的“看守房”,被转到公安局的“拘留所”,最后又被送到矿务局医院“抢救”。因为真相逐渐显露,人们也就没有了当初的“兴趣”。所以我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。
|